音樂付費制度的正當性本就無可置疑,過去數字音樂版權會增加成本,不符合互聯網自由精神只是借口,對付費的抵制或恐懼會因交易雙方的意思自治抵消,因為音樂平臺與消費者關于是否付費或使用何種付費模式尚有商榷余地。付費制度在試圖解決互聯網產業和音樂產業的矛盾時,應避免犧牲用戶的自主體驗,否則將中道崩殂。未來已經來臨,只是尚未流行。
繼今年10月1日天天動聽正式停止音樂播放服務后,阿里旗下的另一重要音樂載體阿里星球在上周二也發布公告,將在近期全面停止APP內的音樂服務。對此,除了轉型為泛娛樂交互平臺的推動力,在規范正版音樂壓力下,阿里星球旗下蝦米音樂和天天動聽的嚴重盜版歷史致使其曲庫出現一定程度的匱乏,也被認為是其“退場”的拖拽力量。
音樂產品的版權認證和付費制度不僅僅讓互聯網音樂平臺之間發生種種你來我往的廝殺,也讓用戶告別過去對任意作品唾手可得的習慣,而不得不同時裝載多個APP,或在“走投無路”時購買數字音樂制品。
數字音樂平臺的版權大戰
實際上,在以國家版權局“網絡音樂運營商應加強版權自律,盡快完成音樂版權的轉授權談判”要求為代表的各種政策背景下,互聯網巨頭們受制于過去盜版泛濫、資源共享的歷史原罪,及迫切打造正版平臺的公共形象訴求,早已在付費音樂的前提——正版音樂版權的爭奪上打的水深火熱。QQ音樂率先與7家唱片公司簽約獨家授權協議,百度與酷我也曾因爭奪綜藝節目的音樂版權鬧得不可開交。互聯網服務提供商試圖脫離以往的版權普通許可模式,紛紛在錄音制品制作領域跑馬圈地,相互指責對方盜用自身正版制品。
2015年5月下旬,阿里向法院申請訴前禁令,稱其260多首歌曲被酷狗盜播,而不到一個月,酷狗也以民事訴訟的方式譴責阿里擅自傳播其獨家音樂。更早之前,網易云音樂就被酷狗起訴,因傳播200余首音樂作品被索賠百萬。網易亦稱酷狗涉嫌侵權共37個案件,要求賠償300萬人民幣。2015年年初發生的混戰不止于此,騰訊起訴網易盜播,網易亦表示對方也曾未經許可傳播200余首獨家作品。這一系列互聯網音樂平臺之間的“互撕”最終以微信封殺網易云音樂、阿里系天天動聽而達到高潮。
以往音樂作品版權在互聯網高速發展初期被犧牲,各種播放器在錄音制品著作權領域“裸奔”,以侵權行為換發展空間的路徑被證偽,而版權爭奪戰之后的音樂付費趨勢將正當化。用戶在企業跟進后也被動的加入正版保護的道路。
但數字音樂播放器很難壟斷所有版權,用戶為某一作品同時使用數種同類產品的體驗也相對糟糕,一輪版權廝殺后,巨頭們也開始版權合作之路,騰訊和網易就在前述法律爭端后達成版權共享協議,而支持這種模式的另外兩個重要原因,一是數字音樂平臺和唱片公司的獨家授權協議通常時間較短,一兩年過后,就會面臨新一輪的比價,因版權的高流動性而喪失用戶黏性想必得不償失。二是花費巨資囤積版權,必然面對消化資金,實現版權紅利變現的壓力,除了直接面向消費者的付費通道,版權分銷亦成為個別坐擁大量錄音制品著作權播放器的當然選擇。
美國與歐洲的著作權擴張案例
著作權人的主動維權和公開發聲行動都是遏制侵權蔓延,甚至拓展權利邊界的嘗試,將之納入司法范疇后,法律認可所發出的指引,可能是里程碑式的判決,也可能是盜版猖獗的罪魁禍首之一。2006年的七大唱片公司訴百度案即是后者,當時,以索尼、華納為首的七大唱片公司發起聯合訴訟,稱百度的MP3搜索下載服務侵犯其專有著作權,百度則辯駁,侵權的是提供盜版資源下載的網站,而非搜索公司。最終法院也判決認可百度向網民提供的是搜索引擎服務而非侵權MP3音樂作品。
與之截然相反,發生在上世紀末的數起美國式數字音樂服務的責任分配爭議,則同樣驗證了司法裁判和商業模式之間犬牙交錯的利益爭執。由于Napster可以將“音樂作品從CD轉化成MP3的格式,并提供平臺供用戶上傳、檢索和下載作品”,曾經由錄音制品制作者掌握的傳播渠道遭到碾壓,用戶利用互聯網可以肆無忌憚的直接或間接傳輸音樂作品。諸多音樂著作權人在發起史上首次針對最終私人消費者的大規模訴訟后,將矛頭指向網絡服務提供商,而法院一審和二審都判決Napster敗訴,稱其必須承擔幫助侵權或替代責任。隨后,第二代音樂共享軟件改變技術設置,脫離了網絡服務提供者的審查控制,試圖從主觀無過錯來合理規避了原判決的侵權要件標準。對此,美國最高法院在新的判例中提出新型獨立的引誘侵權概念,認定“如果當事人散布設備的行為具有推廣該設備侵犯版權利用的目的,例如通過明確表示或者其他積極步驟助長侵權,即應該對第三方因此實施的侵權行為承擔責任。”
在這期間,某在線音樂商店雖致力于推進收費下載,但由于其堅持不使用任何阻止用戶的技術,和著作權人希望借技術手段控制傳播范圍的目標沖突,最終難以與Napster抗衡。而蘋果公司因其提供的錄音制品的格式與當時的MP3播放設備不兼容,打消了著作權人對非法傳播的疑慮,因此iTunes獲得了作品授權。
伴隨技術進步,不斷出現新的傳播方式,而著作權人出于固守原有權利許可模式,傾向控制傳播渠道來保證自身利益,因此新技術誕生風靡常與之發生利益齟齬。例如,美國最初的著作權法頒布之時,音樂作品的著作財產權只包括復制發行,而沒有對公開表演做出規定。100多年后,才將“以營利為目的向公眾表演”納入權利體系,但實踐中“營利性質”認定困難,立法者也認為公開表演有助于復制發行權利最大化,這使實際侵權成為常態。為克服取證復雜、利益分散、維權成本高昂等阻礙,“美國作曲家、作家與出版者協會”得以成立,通過其努力,不僅司法判決認定餐廳酒吧等機構需在演奏音樂作品時向著作權人支付報酬,立法也讓廣播組織為其廣播音樂作品的行為支出費用。
從美國音樂作品著作財產權邊界的擴張歷史看,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免費之路必然會有盡頭,著作權人積極運用既有法律條款或通過訴訟推動判例的維權模式值得借鑒,從“以用設權”的立法路徑,即隨著音樂作品從復制發行樂譜到公開表演,再到廣播和網絡傳播的權利內容的疊加法中可以得出兩個基本結論,一是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免費之路必然會有盡頭,二是但是立法者應防止在權利許可過程中,著作權人對新傳播手段的保守態度導致部分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成為壟斷實體,繼而阻礙音樂作品的傳播效率,影響“物盡其用”。今年11月,德國音樂版權機構GEMA與YouTube持續數年的版權訴訟終于落下帷幕,GEMA原訴求每首歌每播放一次即支付0.375歐分的補償標準,但最終雙方同意放棄所有尚未解決的訴訟選擇和解。考慮到在案件發生之時,歐盟正嘗試修改著作權法,賦予著作權方對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更多的控制權,YouTube此時的和解也算是明智之舉。
歐洲最流行的法國音樂流媒體服務商Deezer就曾透露,向音樂作品著作權人移轉的內容成本占據了公司營收的四分之三,蘋果公司的工作人員在2015年就表示“Apple Music在美國71.5%的營收將被支付給商標、曲作家、藝術家以及其他合法持有者。而在美國以外的地區,該數字還會上升至73%之多。”但公司經營成本的上升并不等于著作權人最終收入水平的提升,今年,美國版權委員會就針對音樂流媒體發布了再次提高的廣播和網絡傳播稅率,其中,免費音樂的新稅率提升20%,至每首歌0.0017美元,但由于付費無廣告音樂的稅率下降,稅率平均提高了15%。
但正如立法需對流動的權利平衡進行謹慎考量,防止一方坐大,著作權人并非永遠扮演著受害者角色。法定使用和合理使用就是對著作權侵權現象的豁免。例如,2014年時英國就規定,用戶出于私人使用的目的,拷貝自己擁有的音樂、視頻、電子書、CD和DVD或轉換數字其格式的行為不屬于侵犯著作權人復制發行權的范疇,這一“私人復制豁免”條款頓時引發軒然大波,結果今年年中,該條例即被撤銷。雖然該條款未能成行,但其設定之初也蘊含了權利用盡原則,即防止著作權人無限擴張其自身權利,并可能多重獲利。
著作權“去產權化”被否定,集中許可補充法定許可
過去的唱片公司和廣播電臺既是占據大量著作權的內容制造者,也具備控制傳播渠道的身份,他們的經濟利益來源于音樂載體的販賣或傳播權利的許可,因而他們更傾向于將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當作一個新型但又傳統的分銷商,并對其侵蝕產業份額生出警惕。對傳統音樂產業的主體而言通過作品獲取版權收益的典型思維天然的指向了付費音樂,這與“草莽時期”比拼流量的互聯網免費自由的大旗天然不容:數字音樂產業發展初期的互聯網服務提供商通過搭建平臺和免費音樂吸引流量,進而向第三方獲取收益。
當然,已經流行的免費通道并不能以習慣為由自動合法化這種忽視產權保護的商業行為,我們甚至可以理解為終端消費者與提供盜版作品的互聯網提供商都曾剝削了音樂作品的著作權人,而平臺因流量獲得的種種收益只不過來自于著作權人應得經濟利益的讓渡。
雖然互聯網經濟中存在自愿“去產權”的公共許可。比如,以維基百科為代表的各種網絡百科應用,構建于用戶自發生成內容并傳播的基礎上,免費的一大激勵來自于已經公共化的產權。但音樂作品想必很難移植此種烏托邦模式,一是錄音制品的著作權人通過授權許可獲益的手段雖經歷技術變遷,但其價值取向未曾消亡。二是目前部分仍舊存在的免費且合法的數字音樂,受制于互聯網服務提供商與著作權人不對等的協商地位現狀,而非后者的心甘情愿。
但增加獲取版權難度的除了著作權人個體數量的龐大,另一難點在于著作財產權種類的復雜無形間增加了授權成本。也正是因此,有業內人士呼吁將復制、發行、出租、廣播、網絡傳播等權利統一為“商業使用權”,再讓錄音制品制作者和互聯網服務提供商通過合同協商分割“子權利”。但反對聲也相當激烈,認為此種投機取巧的方式將得不償失,表示權利的合并會使得原有權利獨立性喪失,且借助合同分割的“子權利”因缺乏絕對性和排他性,更易滋生不必要的糾紛,并由此降低傳播效率,與降低交易成本的初衷背道而馳。不過,一站式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可以解決權利類型和歸屬分散的弊端,我國著作權法在修改時就曾因是否保留錄音制品的法定許可發生過爭議,而最終,社會選擇鼓勵著作權人通過集體管理組織代表,一次性打包授權各種財產權。這種集中許可的優勢在于避免了法定許可導致的著作權人的許可權被剝奪,定價權轉移至行政部門,誘發權力尋租的不正當現象,可以最大限度的自由調整費用標準,遵循市場規律,既方便了終端用戶對音樂作品的合規獲取,也給予著作權人足夠合理的經濟誘因。
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向錄音制品制作者或音樂作品著作權人支付版權費用還只是音樂付費制度的上游,與錄音制品制作者類似,互聯網公司將不單單是付費主體,也將成為面向下游用戶的收費對象。但對于消費者而言,付費音樂并不一定導致用戶需為每首音樂作品支付相應價款,平臺既可以選擇向第三方收取廣告費用,免除因收費驅離用戶的尷尬處境,也可以在向終端用戶收費時依據頻次、數量,包年包月等劃分費用階梯。
盡管音樂版權大戰讓產品價格水漲船高,也有人表示:“音樂版權對于數字音樂行業的影響力,與視頻版權對于在線視頻行業的影響力,處于同一量級。”但后者傳導到上游的高片酬等現象并未復制到歌曲制作者身上。我們反而看到一而再再而三的關于大陸音樂行業不景氣的抱怨,對音樂作品的侵權行為依然俯拾皆是,大眾在多年免費獲取音樂作品的消費習慣下,不僅對以付費為主的正版轉型模式尚存抵觸和僥幸心理,更對眾多維權行動不夠理解或認同。由劉歡、谷建芬、三寶等數十名音樂人組成的著作權代理機構——華樂成盟,向《中國好聲音》發起數起跟公開表演權有關的訴訟,起訴格力電器等侵權主體因“董明珠自媒體”以廣告用途未經許可侵權使用歌曲《因為愛情》,都只是在輿論略微掀起一些波瀾。
創作人難以從作品的版權收益中獲益,自然使得原創者的生產環境相對惡化,原創音樂的品質和數量也就相應下滑。這也難怪不少自詡歌手的演藝人員常常“賣慘”,控訴版權利益分配的不公。黃子韜在本月初的一次頒獎禮上,再一次重復了很多歌手都曾表達的意念,即多數人都認為中國音樂市場目前沒錢賺,他做綜藝拍電影都是為了有機會去做音樂,而音樂才是他“最重要的夢想和人生”。“打廣告、賣衣服、開飯店都是為做音樂積累資金”的薛之謙也曾透露,其歌曲《演員》的點擊率已經破億,但其個人并未從中獲得一分一毫的收入。
結語
總之,音樂付費制度的正當性本就無可置疑,過去數字音樂版權會增加成本,不符合互聯網自由精神只是借口,對付費的抵制或恐懼會因交易雙方的意思自治抵消,因為音樂平臺與消費者關于是否付費或使用何種付費模式尚有商榷余地。付費制度在試圖解決互聯網產業和音樂產業的矛盾時,應避免犧牲用戶的自主體驗,否則將中道崩殂。
在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逐漸摒棄行政門檻,維權行動日漸高漲,實體唱片向數字唱片轉型以及政策合規壓力下,著作權人略有上升的談判地位和大眾對知識產權領域價值位階的嶄新認知,都將有助于互聯網巨頭消化因收費流失用戶的憂慮,并在搶灘正版版權后,加速推進付費音樂。
“未來已經來臨,只是尚未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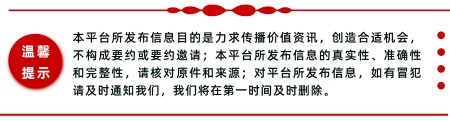
圖片來源:找項目網